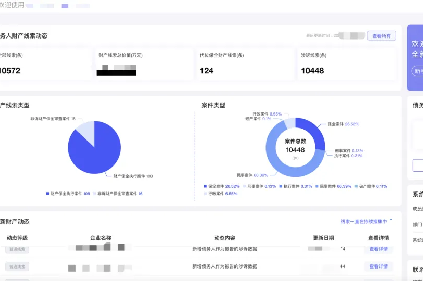蔣陽兵,資產界專欄作者,北京市盈科(深圳)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,盈科粵港澳大灣區企業破產與重組專業委員會副主任。中山大學法律碩士,具有獨立董事資格,深圳市法學會破產法研究會理事,深圳市破產管理人協會個人破產委員會秘書長,深圳律師協會破產清算專業委員會委員,深圳律協遺產管理人入庫律師,深圳市前海國際商事調解中心調解員,中山市國資委外部董事專家庫成員。長期專注于商事法律風險防范、商事爭議解決、企業破產與重組法律服務。聯系電話:18566691717
作者:王洋
來源:資產界
2025年10月,隨著《網絡借貸管理辦法(修訂稿)》正式落地,中國網貸行業再一次站上了重塑與淘汰的臨界點。新規明確要求:綜合融資成本不得超過年化24%,并強化了借貸撮合平臺的持牌管理、資金存管、以及數據安全審查制度。這一條條細則,看似只是監管層的制度完善,實則掀起了一場關乎整個行業命運的“生死時速”。
短短一個月內,多家中小型平臺宣布暫停業務、下線產品或申請轉型為助貸機構。據行業數據顯示,截至10月初,全國存續的網貸撮合平臺數量已銳減至不足500家,相較三年前的高峰期下降超過九成。這種“斷崖式收縮”,不僅標志著網貸行業的野蠻生長期徹底終結,也意味著整個不良資產處置體系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與轉型考驗。
回顧過去幾年,網貸平臺曾是普惠金融的重要補充渠道。它讓無抵押、無信用記錄的小微人群獲得了貸款機會,也為部分高風險資金提供了高收益出口。但這種模式的核心是高風險定價與高速流轉——當年化利率超過30%、40%時,壞賬率依然能被高收益覆蓋。而如今,監管紅線將綜合融資成本壓至24%以內,這意味著平臺失去了“高息對沖風險”的緩沖區。不良資產率一旦上升,平臺將直接陷入流動性困局。
行業人士普遍認為,新規的出臺是一場“硬著陸式的再平衡”。監管意圖明確——遏制過度放貸與暴力催收,規范資金流向、防范系統性風險。但對于很多中小平臺來說,這不僅是合規問題,更是生死問題。過去靠高息驅動的風控模型、資金周轉邏輯、資產打包策略,幾乎都要被推翻重建。
與此同時,新的風險正在顯現。由于部分平臺關閉或縮減規模,存量不良資產開始集中暴露。尤其是那些在2023—2024年疫情后放寬授信、快速擴張的機構,如今面對的是雙重壓力——既要應對監管審查,又要處理堆積如山的逾期資產。據業內測算,僅一線城市平臺當前待處置的網貸不良資產余額就超過200億元,而這一數字仍在上升。
可以說,2025年10月這場政策落地,成為了網貸行業的分水嶺:誰能在合規框架下重構風控與資產管理機制,誰就能活下去;而那些依賴高利率、灰色通道、人工催收的舊模式,則將在新規的重壓下被徹底淘汰。
但真正的考驗才剛開始。監管要求的“合規”,意味著嚴格的資金路徑審查、信貸信息備案、以及第三方存管,這在客觀上延緩了資產流轉速度;而市場要求的“效率”,又逼迫機構必須快速清收、盤活不良、穩定現金流。如何在這兩者之間找到平衡,正成為網貸行業能否走出危機的關鍵命題。
這場變革不是單純的監管行動,而是一場關于時間、風險與信用的博弈。網貸平臺、資產管理機構、以及背后的投資人,都在這條越來越窄的跑道上爭分奪秒。
在監管政策趨嚴、平臺數量急速收縮的背景下,網貸行業的不良資產處置進入了一個復雜、緩慢而充滿不確定性的階段。許多業內人士形容現在的處置節奏是“像在泥里跑步”——看似還在前進,但阻力巨大、效率低下。
最直接的問題,就是周期太長。按照最新行業統計數據,從債權轉讓、司法立案到執行回款,一個中等規模的個人網貸不良資產處置周期平均需要6個月甚至更久。相比于疫情前3個月以內的回收周期,如今的時間成本幾乎翻倍。造成這一變化的原因,不只是案件數量的激增,更在于監管要求的平臺合規存證、合同審查、數據追溯等環節,都被細化成必須經由第三方審計或司法確認的流程。每一步都增加了時間,而時間本身就意味著成本。
同時,收益的不確定性讓投資機構和資產管理公司愈發謹慎。過去,在高利率時代,不良資產包往往能依靠高息溢價、催收分成模式實現快速變現;如今,隨著監管明確禁止過度催收和轉包式追債,原先的收益模型已經失效。一個曾經被估價為“8折收購、9折回收”的資產包,現在可能需要“5折收購、7折回收”才能覆蓋成本,而一旦遇到無法執行的債權,連本金都難以收回。對于那些依賴現金流維持運營的AMC小機構來說,這幾乎等同于斷糧。
更深層的壓力來自法律風險的上升。新規不僅對資金流向提出嚴格要求,還強調了債權處置過程中的隱私合規與催收合規。一旦出現數據泄露、催收越界,平臺及相關資產管理公司都可能被認定為“違規經營”,承擔連帶責任。過去那種以外包催收、灰色中介為主的模式,如今已成高風險地帶。司法系統對債權人權利的保護仍然存在時間差與地域差,地方法院執行難、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依舊突出,許多債權案件在執行階段“卡殼”,形成了新的風險堆積點。
對整個行業而言,這些痛點疊加,正在形成一種新的結構性困局。資產回收慢導致現金流吃緊,現金流緊張又迫使平臺壓縮風控預算,進而削弱新業務的合規投入。長周期、低收益、高風險的循環,成為新規之下的隱形陷阱。
而對于資本市場的參與者,這個變化也極具沖擊力。過往幾年,部分私募基金、地方AMC甚至互聯網金融企業,都把網貸不良資產看作一種“高風險高回報”的另類投資;他們愿意在短期內承擔催收壓力,只為獲取高折價回報。但如今,隨著時間成本和法律風險被重新計入,這種套利空間幾乎被壓縮殆盡。越來越多機構開始意識到,不良資產不再是一個“回款游戲”,而更像是一場合規與流動性的拉鋸戰。
行業在變,邏輯也在重寫。那些還想在新規時代繼續生存下來的機構,必須接受一個現實:不良資產處置的核心,不再是“快”,而是“穩”;不再是“高收益”,而是“可持續”。
當行業的速度被監管按下“慢鍵”,真正的問題就變成:在必須合規的前提下,如何讓處置效率重新提升?這不是一個靠加班或技術“堆”出來的效率問題,而是需要銀行、AMC機構、金融科技公司乃至司法系統共同重塑的一整套邏輯。
眼下,部分先行者已經開始改變傳統的不良資產思路。他們不再把債權僅僅視作一串數字或催收對象,而是嘗試“資產化”地去運營。例如,一些機構在面對大量網貸類個人債權時,不再單獨訴訟、逐案執行,而是將其打包進入資產支持計劃(ABS)或結構化信托,通過風險分層和現金流優先級設計,把原本滯留在賬上的債權,變成可以流轉的金融產品。這種方式雖然前期成本更高,但能極大縮短回收周期,讓不良資產真正具備“市場價格”。
與此同時,金融科技正在成為整個行業的潤滑劑。過去那種人工催收、紙質證據的處理方式,在今天已不具備效率優勢。新一代不良資產管理平臺正通過區塊鏈存證、AI風控建模、電子執行系統等手段,把債權的真實性、合同履約軌跡、催收過程記錄全部數字化。這不僅方便司法認定,也減少了“證據鏈斷裂”帶來的執行失敗。更關鍵的是,科技手段使得資產處置過程的風險敞口被精確量化,從而讓機構在定價和回收策略上更有底氣。
但技術并不是全部。行業要真正走出困境,還得回到合規與合作的底層邏輯。近年來,不少地方政府開始推動地方AMC與法院系統建立“債權快審通道”,讓中小額債權案件能以電子訴訟、批量執行的形式處理,平均結案時間縮短近40%。而銀行、消金公司、互聯網平臺之間,也在嘗試通過聯合催收與數據共享機制,降低重復訴訟、反復追債的摩擦成本。這種協同機制的核心價值,在于讓行業資源不再分散,而是形成“合規共治”的閉環。
當然,效率的提升最終要靠機制上的激勵。現在有些機構開始嘗試“處置與回報掛鉤”的績效模型,不再單純按項目規模定獎金,而是以真實回款率、訴訟成功率作為考核指標。這一變化讓管理者從“立項沖規模”轉向“回收控風險”,整個資產鏈條因此變得更緊湊、更務實。
可以預見,未來的不良資產處置,將從一次性“清理賬面”的被動行為,轉向一個更具戰略性的金融再造過程。那些能在合規框架下重構流程、引入科技、建立跨機構協同機制的參與者,將在這場“慢周期”的博弈中反而贏得主動。因為監管的真正意圖,從來不是讓行業變慢,而是讓它變穩、變真。
當“速度”讓位于“質量”,當“套利”讓位于“管理”,網貸不良資產處置的生意邏輯也許正在被重寫。但新的時代里,慢下來或許并非壞事——它意味著信任重建的開始,也意味著一場更理性的資產清理,正在成為行業新的起點。
注: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,不代表資產界立場。
題圖來自 Pexels,基于 CC0 協議
本文由“資產界”投稿資產界,并經資產界編輯發布。版權歸原作者所有,未經授權,請勿轉載,謝謝!




 資產界
資產界